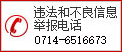“桑葚黑,要割麦”。端午前后,蚕老枇杷黄,又到了该割麦的时候。
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鄂东地区已经很少种小麦、大麦了。春天的田野,只有野麦从未缺席,还在坚守着人们对麦的印象。
小时候的春天,大麦、小麦和野麦是经典的主角,“绿油油的麦苗”是写春天的作文里不能缺少的句子。那时候粮食金贵,土地基本没有时间闲置。收了晚稻就要种麦子、种油菜,春夏秋冬,田地从不会空着晒太阳。
大麦主要是作为米糖的原料,只有会熬糖的人家才会种。小麦则很普遍,家家户户都要种,是早些年结束春荒的救星。每年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,人们几乎都是在数着日子盼到开镰割麦。“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”,割了新麦,标志着已经渡过了春荒,此时,家家户户一定要吃一顿小麦粉做的发粑。而野麦,仿佛是小麦丫环,有小麦处必有野麦。但野麦不受待见,在农民看来,它就是在田地里捣乱的杂草。所以,野麦只能安身于田头地角、荒山野岭。
但野麦从来都不在意这些,从贫瘠的山岗,到低湿的洼地,只要能落脚的地方,它都会顽强地扎下根来,和其他有名字的、没名字的野草在一起,执着地生长。纵然是牛吃羊啃,只要根还在,雨露一滋润,要不了几天,它又露出柔嫩的姿容。
野麦的生命是属于春天的,过了春分,麦苗起身。春分一过,以前还羞羞答答、匍匐混杂在草丛里的野麦就一下子蓬勃旺盛起来,拔节分蘖吐穗,大大方方地展示自己的个性。它的穗张扬洒脱,不像小麦那样拘束紧致,每一株麦穗像豆角一样密密挂满果麦壳,古人形容是“离离结实”。麦壳里孕育着它们延续未来希望的种子。
据古书记载,野麦又叫雀麦,《诗经·尔雅》中称为“蘥”,能“收敛止血、固表止汗”,有很强的药用价值。小时候,虽然不知道这些。但在孩子们眼中,它也是极有用的。
每年早春,放学后,我们一群孩子都要提着竹篮扯野麦,作为猪饲料。如果扯累了,我们就抽出一根野麦茎,掐下刚刚拔节的麦杆,在一端轻轻一捏,做成一个简易的麦哨,噙在嘴里,轻轻一吹,就吹出了好听的声音。
春夏之交,野麦成熟,在田野里随处可见,一株株,一丛丛,金黄色的麦穗,缀满枝头的野麦壳像一个个小小的铃铛,在风中摇曳,炫耀着生命的饱满。这时候,打猪草的孩子就会去“勒野麦”。他们背个竹箩或提个蛇皮袋子,找到一株野麦,用手握住麦穗的底部,再向顶端用力一捋,就收到一把野麦壳。勒回的野麦壳粉碎后就成糠喂猪。那时,养鸡卖蛋,鸡是农家的“油盐罐”,而养猪卖钱,猪是农家的“存钱罐”,一家人过年的行头,孩子们读书的学费,都得从这个“存钱罐”里开支,而让猪吃饱长肥,野麦是很好的补充饲料,也是帮助人们改变生活的功臣。
野麦冬萌春长,一岁一枯荣,像熟悉的老朋友,每年都会准时与人们相会,又都会悄悄地走向人们记忆的深处,等到来年再见的时候,那一定又是一个美好的新开始。